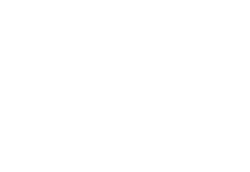單獨 ― 《夜祭》的策展註腳
文:楊陽
中譯:黎健强、楊陽
這 是《夜祭》的策展註腳。就像一般註腳,它是一個文本的延伸;但是,它並非以文字作為依歸,而是屬於展覽的。因此,它留於一個帶著策展性的註脚,關顧著它的 源起 ― 這展覽。這「策展性」跟一般會申明立場和宣佈展覽開幕的「策展聲明」不同 ―《夜祭》並不需要這些 ; 它會自行解說。然而,《夜祭》 仍爲一絲一索的意念與堅執,思想與情緒打開,好讓它要貢獻教育的原意得以維持。真正的教育不在於傳遞指令,而是在於造就有關的事和人最廣闊的發展自我潛力 的空間。在這授與受的意義裡,在這來而有往的流動之中,這個註腳為《夜祭》作伴又結伴,就像光影作坊為《夜祭》作伴又結伴一樣。我並非故作謙遜,只是誠 實。
一、職責所在
或許首先要抗拒將焦點集中於高志强在拍攝些甚麼的慾望,也就是,在某一個意義上,對這些影像宣稱擁有權的慾望。這是困難的,因爲我們這時代,機械自動化使拍攝照片變成一舉即得而非讓記憶沈澱的行爲。高志强的作品的準確性和力量也是困難的另一原因 ― 面對有力的準確性,我們每每急於把它馴服。
能延遲這慾望的話,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就會漲退起來 ― 高志强的作品怎樣達至它們當前的狀況 ― 技巧性、藝術性、政治性、思想性?(至於個人方面,可必須歸於他本身。)
有 天高志强自言自語,說假如蘇珊˙桑塔要寫今天急劇數碼化的攝影 ―《夜祭》也是從這環境鑽出來的― 她會說些甚麼?當桑塔質疑戰爭攝影的暴力程式美學,甚至對紀實攝影的傳統提出全盤批判時,高志强讓紀實與藝術同樣地暴露出來。這是因不能分嚐的內省片刻正 捕逮著單獨的攝影真實。這片刻不是厚待,而是詛咒。如果桑塔顧慮攝影在「旁觀[註一]他人之痛」時被使用為將殘虐自然化的工具言之成理,那麽,當攝影成爲攝影師的同伴,目睹他關注 (旁觀?) 自己的痛楚時,攝影又能否得以再發明?
不要稱這些作品爲「集體回憶」,因爲正如桑塔所說:「嚴格來說,並沒有集體回憶這東西 ― 都屬於集體罪咎感一類的錯誤觀念。但是集體教誨卻是有的。」[註二]。當攝影要尋真理,而不是只求事實,照片就不止於社會所選擇去想的:它們是藝術家的單獨回憶,他選擇將這些回憶曝光時也是要跟它們一起死去;也是說,當那片刻的引力「把作者抽空」[註三],就算是他也無法回來了。
如 果有一種攝影歷史能披露社會以視象不斷作出否定,一種「紀實」之名不足以涵蓋的歷史,那麽高志强的作品就可以(以謙虛的態度)靜靜地和不甘心地(因為他寧 願有其他選擇)擔當一角。面對頽垣敗瓦的世界,一個藝術家還能够做些甚麽?他要令它看來美好易明嗎?還是啞忍無言地等候事情的發生?
引用文學方面的例子,澤巴爾德說:「從被殲滅的世界裡建構美學或僞美學效果的做法,即是要褫奪文學的生存權。」藝術家能够做的不是提供答案或者期望解决,他/她不是去消解,「乃是去揭示衝突。」[註四]某 個意義上,攝影的藝術同樣分擔了這厄劫:那單獨見證的也在宣示他的生存權。所有證供在宣稱擁有真理時都是很準確的。準確性會在甚麽時候變得沉悶呢?這個問 題只有真正的藝術家才會捫心自問。當準確性把他/她的精力抽空時,他/她可以重新開始 ― 謙虛地、誠實地、慢慢地、嚴謹地。
二、逼不得已
當高志强命我策展《夜祭》的時候,我腦海中立刻在「策展」一詞加上引號 ― 一個自身已是內外通透的展覽(人物、主題、時間、地點、原因、方式),還有甚麼可以策展呢?寫著這些文字,讓我發覺那引號吸納了不同的意義。它們都是我給嚇住的標記 ― 藝術家和他在一揮手間供承了那麽的多(友誼、歷史、教育、藝術)。給嚇住的感覺既可以叫人癱瘓,也可以叫人啟發:我逼不得已,就跟各位分享些雞皮疙瘩吧。
[註一]桑塔著作的英原題是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. “Regarding”有譯「旁觀」, 也有譯「關注」,英文的regard, 正包含雙重意義, 一方面, regard於 ”regarding a certain matter”或是 ”with regard to…” 這類用法時, 話語的主體和對像分開, 也顯露西方哲學思想中「理想觀察者」(ideal observer)和「非功利觀察者」(disinterested observer)的傳統概念 , 這方面西方女性主義一直提出批判; 而regard於 ”I regard my teacher highly” 或是“This regards me” 等用法的時候, 就有我作爲主體對人和事寄以關注的意思。 桑塔在書中提出紀實攝影以關注之名成爲了非功利觀察者的同謀, 旁觀他人之痛, 此命題也同時迫使她自己的著作接受同樣的質疑,這是桑塔的批判性有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。
[註二]Sontag, Susan,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. New York: Picador, 2003: 85
[註三]Sebald, W.G.,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, London: Penguin, 2003:195.
[註四]Sebald, W.G. cited in slavick, elin o’Hara slavick, Bomb after Bomb, a Violent Cartography, New York: Charta, 2007:98.
強夜深人未靜
文: 黎健強
夜,從來都是屬於聲音的。白天有太 陽,有光,是屬於看的時段;夜晚雖然也有月亮星星,畢竟照明有限,耳朵仍是佔了中風,聽到蟲叫、風聲、人車喧鬧。夜鶯的歌喉令人陶醉眷戀,日間的雲雀、畫 眉鳥和鵲鴝,知音者可就少了。我升中二那年的暑假跟隨祖母首次往父母的故鄉,日落之後最感受到城市和農村的分別:沒有路燈的鄉村真是伸手不見五指,只倚靠 田裡青蛙的鳴叫和同行幾個人的步伐聲,給自己壯壯膽。
今趟高志強展出的黑白攝影作品,全部都是香港夜晚的照片。系列起先只有英文 題目,就叫做《夜曲》(Nocturne)。從一九七八年起高志強就活躍於香港的攝影界,得過多個獎項,也曾經任教於理工學院、攝影中心和藝術中心;但是 自從一九九七年的《藍調》之後,他已經足足有十一年沒有舉行個人攝影展覽了。
法國著名攝影家昂利˙卡泰爾―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)曾經認為,照相機是他眼睛的延伸。不管我們是否認同他,攝影術畢竟是利用光線來製成圖像的,是給看的,是很白天的。事實 上,自一八三九年問世以來,絕大多數製成的照片都是利用陽光拍成。十九世紀時的攝影室,全部設於樓房的天台上:它們主要拍攝人像,上午九時或十時開始營 業,到了下午四、五點,就相繼關門下班去了。
夜晚的照片要到一九零零年前後才有較多成功的例子, 這或者跟底片由溼片進化為乾片,和藥膜感光度提升有些關係。譬如英國的保羅˙馬丁(Paul Martin) 及美國的艾佛˙斯特格列茲(Alfred Stieglitz),他們藉著雨後溼漉反光的路面,讓點點街燈和樹木或銅像的剪影穿梭交織,令人想起勃拉姆斯(Johannes Brahms)的協奏曲。
至於香港,開埠時就有了醜小鴨的形象。沒有來過此地的英國外交部長巴麥尊伯爵(Lord Palmerston),曾經嘲貶香港島是塊草木稀疏的岩石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第十三任總督彌敦(Matthew Nathan),卻說香港其實極富天然美,只是大家都只以它為賺錢工具,沒有注意到原來天鵝已經長出一身漂亮的羽毛了。
香港攝影歷史的研究目前仍處於很初始的階段,從圖像來看,早期的照片都是在日間拍攝的;但是有可能在二次大戰之前,已經有攝影師嘗試拍攝香港的夜景了。到 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,香港的夜景被公認為世界美景;那時候喜歡攝影的人,大概都曾經晚上在太平山頂、尖沙咀海運大廈等地豎起三腳架,拍攝這城市的萬家燈 火。此外每年聖誕節和香港節的燈飾,也是許多拍友的喜好。如果要用音樂來比喻這些照片,我想到的是「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」的《青春舞曲》大合唱。
當時流行的是畫意攝影,即是俗稱的沙龍攝影,講求簡單的唯美視覺效果,以及仁義倫理的道德價值。在這種風格制度的籠罩之下,攝影作品每每大同小異以至重複,即使攝影師們的觀察取捨也趨向於高度的同質性。前段我說的大合唱,就是這個意思。
到了一九八零年前後,香港的藝術攝影的變化漸趨明顯,新一代冒起的攝影人擺脫以往畫意風格的愈來愈多。一方面固然是這些戰後出生的青年人的成長環境與歷 練,使他們不能毫無保留地接受那已變得很僵化的畫意攝影美學觀念;另一方面,他們有機會接觸到西方在畫意主義以外的攝影風格,特別是好幾位曾經在北美或英 國修讀的攝影師回到香港,藉著其作品與教育工作,推動了新一輪的現代主義攝影。
高志強正是當時的一名「海歸派」,其他重要人物還有陳贊雲、王禾璧、吳漢霖、馮漢紀等。他們的攝影美學並不完全相同,但起碼有兩點是一致的:其一是主張直 接攝影,即是攝影師毋須遵照傳統的繪畫構圖,可以直接根據眼睛觀察世界而拍攝;其二是反對盲從模仿,強調攝影者要建立個人獨特的作品風格。三十年來高志強 的攝影風格一直相當貫徹,將現時定名為《夜祭》的系列跟畫意時代的夜景照片比較就很清楚,這絕對是特立獨奏的一把弦琴。
今趟展出的照片近二十幅,除了都是夜間在香港拍攝之外,各照片在地點內容等方面差別頗大;然而在高志強強烈的個人風格 ― 明朗的線條、詭異的光影色斑、壓迫性的鏡頭 ― 統攝之下,渾然有一種整體性的分陳與協調。各場景儘管少見有人或者動物,但總是或顯或隱地像有些能量蠢蠢欲動:滿地落葉、一隻扁舟、山坡的水漬、利東街的 廣告招牌,彷彿都作著嘈嘈切切的聲響,不容許夜間寧靜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極具影響力的攝影家邁納˙懷特說攝影師的創意有兩種,一是揭示被攝物的性 格,二是通過被攝物表達攝影師的思想。從《夜祭》來看,高志強無疑屬於後者。
「香港是個生機旺盛的城市;不見死亡的形跡。到處都是車輛,喇叭按得老響,到處都是人,扯大喉嚨呀呀呵呵的講廣東話;彷彿一切永不止息。香港是一個午夜一 時海底隧道都會塞車的城市。」本地作家黃碧雲大約二十年前寫了《衰亡勢》一文,覺得香港恐怕會盛極而衰。今天,我看到的正是憂慮衰亡的錄音。
三十年攝影、三十年攝影教育―訪高志強
楊陽錄
一、七、八十年代加拿大和香港的攝影教育
楊: 你七十年代在加拿大接受的攝影教育是怎樣的?
高 : 是一所fine arts school。 攝影學校有幾種,有些可以是很商業的,例如美國的Arts Centre、Brooks 那些,是訓練學生畢業出來當商業攝影師。 但另外一類就是如我所就讀的Banff Centre,是一所Fine Arts School,除了攝影,還有音樂、寫作、 舞蹈。學校當時是用攝影的技術作爲基礎,同時滲透設計、藝術史、攝影史的課程。有些是很技術性的,又要計數,又要學畫圖表,很討厭。但都捱過了,成績還不 錯。
這所學校是我偶然發現的,當時我正在當攝影助手,那時香港沒有攝影教育,只有沙龍,不是我想要的,我就只能讀設計, 進大一設計學院,跟隨王巫邪學畫,也跟隨梁巨廷,他教懂我絲印,又到中文大學聽呂壽琨講課,後來轉去了當攝影記者。當時畢業已經兩年多了, 我找到Banff那所學校,除了是 School of Fine Arts ,我看到學校的小冊子差不多要暈過去!因為Banff實在太美麗了!雪山上有所古堡,學校就在旁邊。我覺得一定要去讀書,就送作品選輯過去,那時候我送了 拍攝黃大仙的一輯,後來考到了 。
楊: 學畫對你攝影有影響嗎?
高 : 有,設計也有,因為藝術有很多東西是貫通的,比方平面設計上的點、線、面跟攝影是很有關係的,還有當時那群冒起 的藝術家搞了大一這所學校也發揮了作用。攝影的技術是科學,其他的都是藝術修養和刺激,對我幫助很大。當時Banff Centre有藝術家也有設計師任教,教育是很全面的。他們不期望我們畢業要做攝影師,你得到了教育就自己發揮。
楊: 你當時的同學是怎樣的?
高 : 三年來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和香港人,整個學校的藝術氣氛非常好。因為接觸的人是畫家、 作家、 搞音樂的人,晚上悶了,就到外面聽人家jam音樂。當時的Banff Arts Festival,整個城市都是藝術,有芭蕾舞、戲劇等等,接觸的層面很廣,我真的沒選錯。但很可惜,在大約1981年,整個大樓燒毀了,它再沒有開了。 但最近我竟然剛收到一個電郵,學校reunion ! 哈哈! 十一年來畢業的學生回去,也有教授,我應該會回去,九月的Rocky Mountain 特別美!
楊: 講回來, 香港攝影教育當時是怎樣的?
高 : 我回來之後,徐子雄替我搞了第一個展覽,在American Library。 是1978年。同時,王巫邪叫我回理工教攝影,作為畫家,王巫邪的理念是設計課程要純藝術(fine arts)多於設計。 那時候張義、郭孟浩也正在任教,所以是用純藝術作基礎混合設計理論去教的,很好玩,因為藝術氣氛很好。第二年分科,我進去教了大概一年的日校,但不是全職 的,年紀太少了,不行,外面的社會是怎樣還未知道。當時跟學生打成一片,因為他們年紀跟我差不多,都混在一起,林敏聰在我班裡面,我們會一齊去大陸旅行。 後來理工搞了一個Applied Photography 的課程, 爆得不得了, 很熱鬧.
楊: 來報名的是甚麼人?
高 : 我們當時只收二十人,但申請的有差不多一千人,有些是在職的,甚至政府新聞處的官員都有,因為真的沒有正統攝影教育,那個是第一個在香港出現的正式課程, 所以很多人報讀。教授課程的是在職攝影師,所以學生畢業的時候就是很實在的攝影師。但這個課程忽略了藝術那方面。我當時跟馮漢紀感覺到,千多個學生,理工 只收幾十個,其他人沒有出路,機緣巧合,就成立了Fotocine,位於灣仔酒吧林立的地方。後來, 租貴了, 我們又搬到半山區的堅島,成立了Photo Centre (攝影中心),我們把理工的應用攝影搬了過來,但又加了純藝術的課程,比方藝術攝影,時機很配合,因為香港對讀過攝影的人的需求很大,剛好理工的結構定下 來了,又有一班從外國讀完攝影的人回來,集中在香港,他們都來任教,我們也有跟中大搞文憑課程。
楊: 多年來,你覺得自己受過誰或是怎樣的影嚮,又怎樣影想你教授攝影?
高: 當時跟呂壽琨學畫,三個字:守、破、立。守著法則,破這法則,再立自己的法則, 這三個字對我今時今日還是受用的,好「正」! 但當然, 現在人老了,你發覺太陽之下無新事,你做的肯定是重複前人的,但無所謂了,只要忠於自己。學校給我很多機會,它不會說甚麼好甚麼不好,我回來教書都用這方 法,我不會告訴學生甚麼好甚麼不好,也極力避免告訴他們我喜歡不喜歡甚麼,因為很主觀的,老師說他喜歡甚麼,學生很自然就會向那邊走,Banff Center沒有這樣,我自己可能有設計的背景,不自覺地, 攝影的手法都有點設計味道,像平面設計、對稱等等,有段時間我就問自己為甚麼那麼乖跟隨傳統。後來我覺得又「無壞」,當我把相片攤在地上看,看到自己還是 能把訊息帶出來的, 那就沒問題了。我也不自覺地會受幾位攝影師影嚮,這是無可否定的,他們就是Josef Koudelka、 Eugene Smith、 Bruce Davidson等等。
二、數碼攝影的衝擊
楊:你看數碼攝影怎樣?
高:很多東西好像還未成熟,我的意思是有新的衝擊,但也帶著舊的沉積物,未有磨合,然后你又看到全新的出來,好像國內的, 香港也有,全新一代電腦人出現,他們沒有以前的基礎,可能完全沒有接觸過菲林,相紙,未試過,等於音樂現在一出來就是數碼的。
楊:但數碼攝影者也有探索本身媒體的可能罷?就像你們當年探索攝影一樣。理論上是可以的吧?
高:現在往往走了捷徑,我不是反對它,只是針對新的媒體,比方以前你用針筆畫一條線是可以很直的,現在有電腦就可以了,你不可能否定電腦的好處,對嗎?你不可能回到用手畫的時期,科技能做的是向前的,只不過我覺得現在還未見到數碼攝影方面的成就。
楊:那介面又怎樣?人和機器的介面?Touch 方面?
高:就是未成熟,全都通過電腦。以前全是人手觸摸的,現在全部東西放在電腦裡面,沒有它就做不到。等於畫畫,不能說電腦不好,它帶來很多捷徑,商業攝影方面有 了電腦是很好的,好像電影,以前想不到的影像,現在用電腦全都能做出來了, 恐龍復活呀甚麼呀,都天衣無縫,在我們的年代是不可以想像的。但我是說,電腦其實包含了我們以前攝影的 craftsmanship,現在用了電腦表達,我不是說要用舊的東西,但真正能用數碼攝影表達自己的作品我還未見到,可以這樣說,它仍然只停留在影像方面。影像很厲害,就是影像飛來飛去,甚麼都做到,但欠缺了藝術性和哲學性,可能要時間。我相信每個新媒體的出現是要時間的。很簡單,我所見到好的、有深度的攝影作品,都在數碼來臨之前的。我也有問自己是否老了還是落後了,哈哈!其實我都很想看到新事物,但有些我真的不明不白。
楊: 有了數碼製式之後,你覺得人和科技的關係怎樣?
高:我覺得怎說也好,人是最重要的,無論你用甚麼科技也好,人的創作是最重要的,你只是借助一個工具。現在對科技有點濫用。所以我同意讀設計應該從繪畫開始。
楊: 如果你今天要設計新的攝影課程, 你會怎樣?
高: 一定要CS3, Photo Shop,但也一定要有攝影史,一定要,我讀書的時候上攝影史課一定睡覺,圖片又模糊,當時真的悶得我要死,但現在我覺得是很迫切的,因為你不明白過去就不能面對將來,現在中國攝影的新一群好像有這情形,也不光是攝影,畫也是, 很明顯,全是大頭公仔,我最擔心的是那些買家, 炒家。這現像很奇怪的,在故宮的藏畫可能價值不及一個年青的畫家得作品。
謝: 我最近讀過一位美國攝影評論家用「cloning」複製這字眼來形容新攝影,就是沒進步,原地踏步。你會看到很多人去分享去旅遊等等的照片,但都是千篇一律的。那不是創作,是不停重覆一個動作,而它的影響就是把本來是假的東西變成真的,就是說:一張廣告照片,本來它就是假的,叫你要穿這個,吃那個,但通過不斷的重覆,其實在重覆一個假像,因為你不是生存其中。現代人就不是生活在現實,而是在⋯⋯
高:虛疑現實。我同意,加上傳媒的加速,還有YouTube……
楊: 但YouTube也有很好的。
高: 對,間中吧,我也有看。但大部份是很重覆的。
三、回到自己
楊: 是不是正正為了這些,你要往夜裡尋找新的東西?
高:其實我是第一次拍攝晚上。以前都是為了工作,旅遊協會的東方之珠那種,哈哈!因為九七的改變,傳媒的轟炸太厲害了,我突然覺得要退避,由拉得很盡很緊, 突然要放鬆,我就很多場面都不出現,特別是商業方面的活動,除了教書,很多職務都辭掉,偶然跟老友見面。看晚上的東西我蘊釀了很久,我相信每一個攝影師對晚上一定會有感覺,但未必會進行拍攝。以前我拍的,好像六四的時候,我看著事情在面前過去,但在晚上,我坐著,站著,可以慢慢靜下來看世界的改變。其實充滿著囉嗦!
楊: 可以多說一下你剛才說近年轟炸的感覺是來自甚麼?
高: 比方我看奧運真很厭煩,真想看誰會弄滅那個火,哈哈!我每年回北京約五次,中國實在離普,瘋狂,外國最奇怪的建築都在這古都產生了,扭曲的建築等等的。 全世界的焦點放在這裡,好比要奉承一個朝代的來臨。九七香港是這樣,現在也是,香港每個人都姓「利」的了,所以我看得很厭煩,要脫離,夠了夠了,不要再來。傳媒也是,特別是黎智英搞了壹傳媒之後,真的是一種轟炸。還有,你想去公園坐一下都要看倒數鐘。
楊: 最後回到你的作品,你一向跟你拍的對像的距離是很近的,凝視的角度往往是正視,甚至有點對抗的,你可以說下嗎?
高 : 對的,我們這代是比較「兜口兜面」的, 我想是攝影給了我勇氣。